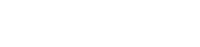无尽的悲伤,之后便是一阵短暂的恐惧。
我突然再次想起之前坚定了的那个想法,却又看见落地窗玻璃后,那美丽的窗帘后面,仿佛有两个人影在剧烈晃动——他们显然是在争吵。
他们在争吵着,我却只想看见他。
一个多月前,我第一次见识到钞票的威力并花费一笔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,足以支撑大半年开销的‘零用钱’,从那家国际化医院里偷偷出来的时候,第一次看见了站在落地窗后的那个男人的身影,那个让我觉得有点熟悉的身影。
我不是土豪但我嫁了个死去的土豪,所以零用钱忒多了些。
半月前,我又一次次花费零用钱从那家国际化医院里偷跑出来的时候,第一次看见了那扇偌大的落地窗后面,还有一个女人,觉得她的身影很像我认识的一个女人,但一时想不起,那个女人,到底是我曾经认识的谁。
几天前,我无意间看见那个女人从别墅中疯走出来,她手里提着个粉色行李箱,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,身上只一件白色t恤,我清楚地看见,她离开别墅前,朝我微笑,却被活活吓个半死。
因为她和我,长得一模一样。
因此我不想见她,但我想见他,便不得不强迫自己将目光流在那里。
☆、bsp;17
他们在不停地争吵,我似乎听见了玻璃杯碎裂的声音,电饭锅撞击微波炉的声音,智能电视机碎屏的声音,他们彼此捶打怒骂对方的声音,这些声音此起彼伏,有点像一场恐怖电影里的背景音乐,恐怖至极,却又不如电影里的那些旋律和谐。
可不知为何,我却不是很害怕。
继而,我看见了红晕的烛光,我看了血红色的枕头,我看见了锋利的锋芒,我看见了嫩白的柔荑,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跳跃着,翻滚着。
隐约中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,我顺着那个声音的方向望去,画面定格在了一间熟悉的卧室。
幽暗暧昧的卧室内,红晕的烛光,如死灰般沉寂,血红色的枕头下面,闪过一丝锐利的锋芒。
是一对痴男怨女…… 她爬着,背对着他,双手悄悄缩进枕下,身体微微地颤抖着。
他非常粗鲁地褪去她身体的最后一道防线,将那布满蕾丝花边的幽暗色随手一抛,便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。
他不停地索取着,她不停地颤动着。他看着她雪白稚嫩的背部肌肤上,在微弱的烛光中轻轻颤动的点点疤痕,眼里闪过一丝怜悯,却又瞬间充满血丝,再也没丝毫的怜悯之意。
有那么一瞬间,他停了下来,眼神里却充满了莫名的冷漠和淡然的诡异。
她明白他想做什么,自从她的温姐姐,他的初恋自杀后不久,他便一直这样对她。
他熟练地从床头柜上一把抓起还在燃烧着的红烛,动作就像小猫突袭老鼠那般迅捷和灵敏,却没有半滴蜡油从蜡烛上散落。
当他将晶莹的蜡油,一滴一滴“倾泻”在她雪肤上那些斑驳的疤痕之间时,她只微微闷哼了几声,便问他,“苏亦然,你真的,有那么爱她吗?”
他没有回答,动作却更加粗鲁,眼神越来越冷,但她还在注意倾听。
可是,伴随着肌肤碰撞声的,只有她硬生生咽到嘴里的诡异嘲笑,那声音凄凉无比,只可惜他丝毫没有听到。
或者说,他在假装丝毫没有听到。
她的闺蜜自杀后的数月里,他从没一丝和她□□的欲望,他却夜夜变着戏法折磨她。她无时无刻想要离开他,但她却日日期盼地忍着他——她时常会想起的男人。
他记恨她,在他眼里,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一个初恋。
她抱怨他,在她眼里,是他和她的闺蜜,一起背叛了她。
当他精疲力尽的瘫在她怀里抚慰的时候,她悄悄将左手伸进枕下……他似乎没察觉到,却对我露出了一个微笑,那个微笑诡异而神秘,让我不寒而栗。
我从幻觉中惊醒,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,记起了苏亦然并不只像我记忆中那样美好,却不明白在这个幻觉里,他为何要冲我微笑,若是那一晚他没睡着,又为何要假装睡着?
我想确认自己的想法,却始终想不起之后,具体发生了些什么。
最近,我十分害怕,和邱亦泽相处的这大半年,我发现他很爱我,对我们继承的巨额遗产,他似乎没多大兴致。
那些梦里琐碎的片段,让我恢复了大半记忆,此前画面却始终定格在,苏亦然精疲力尽地摊在我怀里那段,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回想,都记不起什么。
我本想报复邱亦泽,是他将我从楼上推下来的。一周前,我却开始犹豫了,我始终在想,那样做,到底值不值。
可昨夜,当一幕幕在脑海里清晰回放的时候,我便不再犹豫了。
幽暗的卧室,红晕的烛光,锋利的匕首,几个月来,深深印刻在我脑海,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些记忆,或者说,我不愿相信,不敢面对现实,所以那些记忆里的画面,始终定格在苏榆精疲力尽地摊在我怀里那段。
但昨夜,这个画面逐渐完善。
一道锐利的锋芒凌空起落,苏亦然闷哼一声,鲜血自自他胸前奔流而出,缓缓蔓延开来。我双手满是鲜血,眼前一片血红色,血香弥漫了整个卧室,泪水自心底奔流而起,却始终夺不出眶来,内心的解脱转化成各种情绪,不安、愤怒、惊慌、恐惧不停地充斥袭来,我的身体随之不停的颤抖,接着便是,暴躁、狂乱、疯狂直至冷静下来,眼前只剩一片血色,接着便晕了过去。
是我亲手杀了他——我曾经深深爱着的男人,即便那时他那样对我,这个事实,依然无法改变。”
郑晓渝颤抖了一下,她又想起这一幕幕。她缩回血迹斑斑的小手,缓缓移到怀里躺着的那本《山海经》上,抚摸着,好像舍不得拿起它,鲜血模糊了它的封面,泪水欲将它洗净……
一瞬间,她含泪笑了笑,将血色浸染的它突然举过头,使劲朝身后扔,反复在实验般,扔完便冷冷地扭头,看它掉在了哪里。
如她所想,那本被血色浸染的《山海经》,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别墅楼下一块六边形名贵大理石上——那是她第一次跳楼后晕倒的地方,她笑了笑,笑容如几天前她去佛堂祈福,佛祖对她的笑容那般,诡异而神秘。
六个多月来,这本她之前一直舍不得翻开的《山海经》,一直像她最亲的、没有死去的闺蜜那般,默默地陪着她,她只要痛苦的时候,便会拿出来看看。
因此,那些痛楚的恶梦之余,她也经常梦见些开心的事情,比如说,她常常梦见,她像天神那般,自由自在地飞翔。
片刻之后,她娇小惨白的
我突然再次想起之前坚定了的那个想法,却又看见落地窗玻璃后,那美丽的窗帘后面,仿佛有两个人影在剧烈晃动——他们显然是在争吵。
他们在争吵着,我却只想看见他。
一个多月前,我第一次见识到钞票的威力并花费一笔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,足以支撑大半年开销的‘零用钱’,从那家国际化医院里偷偷出来的时候,第一次看见了站在落地窗后的那个男人的身影,那个让我觉得有点熟悉的身影。
我不是土豪但我嫁了个死去的土豪,所以零用钱忒多了些。
半月前,我又一次次花费零用钱从那家国际化医院里偷跑出来的时候,第一次看见了那扇偌大的落地窗后面,还有一个女人,觉得她的身影很像我认识的一个女人,但一时想不起,那个女人,到底是我曾经认识的谁。
几天前,我无意间看见那个女人从别墅中疯走出来,她手里提着个粉色行李箱,穿着一条深色牛仔裤,身上只一件白色t恤,我清楚地看见,她离开别墅前,朝我微笑,却被活活吓个半死。
因为她和我,长得一模一样。
因此我不想见她,但我想见他,便不得不强迫自己将目光流在那里。
☆、bsp;17
他们在不停地争吵,我似乎听见了玻璃杯碎裂的声音,电饭锅撞击微波炉的声音,智能电视机碎屏的声音,他们彼此捶打怒骂对方的声音,这些声音此起彼伏,有点像一场恐怖电影里的背景音乐,恐怖至极,却又不如电影里的那些旋律和谐。
可不知为何,我却不是很害怕。
继而,我看见了红晕的烛光,我看了血红色的枕头,我看见了锋利的锋芒,我看见了嫩白的柔荑,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跳跃着,翻滚着。
隐约中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,我顺着那个声音的方向望去,画面定格在了一间熟悉的卧室。
幽暗暧昧的卧室内,红晕的烛光,如死灰般沉寂,血红色的枕头下面,闪过一丝锐利的锋芒。
是一对痴男怨女…… 她爬着,背对着他,双手悄悄缩进枕下,身体微微地颤抖着。
他非常粗鲁地褪去她身体的最后一道防线,将那布满蕾丝花边的幽暗色随手一抛,便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。
他不停地索取着,她不停地颤动着。他看着她雪白稚嫩的背部肌肤上,在微弱的烛光中轻轻颤动的点点疤痕,眼里闪过一丝怜悯,却又瞬间充满血丝,再也没丝毫的怜悯之意。
有那么一瞬间,他停了下来,眼神里却充满了莫名的冷漠和淡然的诡异。
她明白他想做什么,自从她的温姐姐,他的初恋自杀后不久,他便一直这样对她。
他熟练地从床头柜上一把抓起还在燃烧着的红烛,动作就像小猫突袭老鼠那般迅捷和灵敏,却没有半滴蜡油从蜡烛上散落。
当他将晶莹的蜡油,一滴一滴“倾泻”在她雪肤上那些斑驳的疤痕之间时,她只微微闷哼了几声,便问他,“苏亦然,你真的,有那么爱她吗?”
他没有回答,动作却更加粗鲁,眼神越来越冷,但她还在注意倾听。
可是,伴随着肌肤碰撞声的,只有她硬生生咽到嘴里的诡异嘲笑,那声音凄凉无比,只可惜他丝毫没有听到。
或者说,他在假装丝毫没有听到。
她的闺蜜自杀后的数月里,他从没一丝和她□□的欲望,他却夜夜变着戏法折磨她。她无时无刻想要离开他,但她却日日期盼地忍着他——她时常会想起的男人。
他记恨她,在他眼里,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和一个初恋。
她抱怨他,在她眼里,是他和她的闺蜜,一起背叛了她。
当他精疲力尽的瘫在她怀里抚慰的时候,她悄悄将左手伸进枕下……他似乎没察觉到,却对我露出了一个微笑,那个微笑诡异而神秘,让我不寒而栗。
我从幻觉中惊醒,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,记起了苏亦然并不只像我记忆中那样美好,却不明白在这个幻觉里,他为何要冲我微笑,若是那一晚他没睡着,又为何要假装睡着?
我想确认自己的想法,却始终想不起之后,具体发生了些什么。
最近,我十分害怕,和邱亦泽相处的这大半年,我发现他很爱我,对我们继承的巨额遗产,他似乎没多大兴致。
那些梦里琐碎的片段,让我恢复了大半记忆,此前画面却始终定格在,苏亦然精疲力尽地摊在我怀里那段,无论我如何努力地回想,都记不起什么。
我本想报复邱亦泽,是他将我从楼上推下来的。一周前,我却开始犹豫了,我始终在想,那样做,到底值不值。
可昨夜,当一幕幕在脑海里清晰回放的时候,我便不再犹豫了。
幽暗的卧室,红晕的烛光,锋利的匕首,几个月来,深深印刻在我脑海,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些记忆,或者说,我不愿相信,不敢面对现实,所以那些记忆里的画面,始终定格在苏榆精疲力尽地摊在我怀里那段。
但昨夜,这个画面逐渐完善。
一道锐利的锋芒凌空起落,苏亦然闷哼一声,鲜血自自他胸前奔流而出,缓缓蔓延开来。我双手满是鲜血,眼前一片血红色,血香弥漫了整个卧室,泪水自心底奔流而起,却始终夺不出眶来,内心的解脱转化成各种情绪,不安、愤怒、惊慌、恐惧不停地充斥袭来,我的身体随之不停的颤抖,接着便是,暴躁、狂乱、疯狂直至冷静下来,眼前只剩一片血色,接着便晕了过去。
是我亲手杀了他——我曾经深深爱着的男人,即便那时他那样对我,这个事实,依然无法改变。”
郑晓渝颤抖了一下,她又想起这一幕幕。她缩回血迹斑斑的小手,缓缓移到怀里躺着的那本《山海经》上,抚摸着,好像舍不得拿起它,鲜血模糊了它的封面,泪水欲将它洗净……
一瞬间,她含泪笑了笑,将血色浸染的它突然举过头,使劲朝身后扔,反复在实验般,扔完便冷冷地扭头,看它掉在了哪里。
如她所想,那本被血色浸染的《山海经》,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别墅楼下一块六边形名贵大理石上——那是她第一次跳楼后晕倒的地方,她笑了笑,笑容如几天前她去佛堂祈福,佛祖对她的笑容那般,诡异而神秘。
六个多月来,这本她之前一直舍不得翻开的《山海经》,一直像她最亲的、没有死去的闺蜜那般,默默地陪着她,她只要痛苦的时候,便会拿出来看看。
因此,那些痛楚的恶梦之余,她也经常梦见些开心的事情,比如说,她常常梦见,她像天神那般,自由自在地飞翔。
片刻之后,她娇小惨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