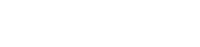屋三门具开,赵庸伯身着族服,先祭拜完祖先,然后才转过身来道:“请出祖娘。”
他的话音一落,只见牌位后面的布幔被徐徐拉开,露出里面一尊脚踩□□的金塑神女像,所有的村民立即纷纷跪下叩头,现场里站着的便只剩下了杨雪仕跟昭然两个人。
旁边立时有人不悦地道:“请两位也给祖娘行礼。”
昭然脸露为难之色:“老婆子我可是巫王弟子,这要是拜了祖娘,他老人家不高兴了怎办……”
他话还没说完,只见杨雪仕倒是上前作了一揖,上了一柱香,昭然无语,只好跟着也作了一揖,上了一柱香。
赵庸伯一直淡然无语,此时方才道:“今日召各位族老来,为着两桩事,一桩是当年赵景强/奸冤案,一桩是为着秀英身死案。”
族老们齐声道:“听从族长的吩咐。”
“让赵应文,赵敏儿进来。”赵庸伯从盘子中拿出了一块门牌。
昭然将凑过去细看了一下族老们手里的木牌,发现他们手里木牌其实每个人都略有些不同,赵字还有几个细小的数字,显然是为了区别用的。
赵敏儿浑身戴孝地走了进来,身后跟着两个护院拖着赵应文,一个晚上赵应文形貌全毁,头发散乱,双目无神,哪里还有当初斌斌文士的模样,他嘴里不停反复地道:“别杀我,别杀我。”
赵庸伯看着手里的门牌道:“你在府内与绣娘有奸/情可承认?”
“我认,我认。”赵应文浑身哆嗦地道。
“秀英你是怎么杀的?”
赵应文双目无神地道:“她说我如果不休了妻子娶她当正房,她,她就要告发我是□□罪,我一气之下就跟她扭打了起来,然后就将她给掐死了,最后我,我怕她还没死,就用刀子又插了她一刀。”
赵庸伯抬头道:“赵应文通奸罪在前,杀人罪在后,罪大恶极,需报官处理,其家族念其老母稚儿无辜,逐其村落外居住,族老可有异议,若无异议就举牌。”
族老们纷纷举牌,无人有异议。
赵庸伯将手中的木牌丢到了旁边的碳火盆中,赵应文整个人抖成了一团。
杨雪仕见旁边昭然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,他小声问:“你又在想什么?”
昭然却举手道:“我有异议。”
“你又不是荡渔村的人。”旁人道。
昭然嘻嘻地指了一下杨雪仕:“但是你们不是邀请我们大人了吗,那我们总可以提一些意见吧。”
“你又是谁?”
“我是替杨大人说话的人。”昭然理所当然地道。
杨雪仕瞧了他一眼说了两个字道:“不错。”
赵庸伯抬手制止了下面的议论声:“你想说什么?”
昭然笑道:“我想说的话,需要传一个证人。”
“你想传的证人是谁?”
“阿大。”
“阿大……”赵庸伯道,“阿大昨日已经不知去向,你如何传召他?”
“现在我知道他在哪里了,因为有人留了条线索给我。”
“阿大在哪?”族老们议论纷纷。
昭然指着那尊祖娘道:“在那!”
众人抬起头,赵庸伯眼神微微一变,那尊纯金的女神像上眼珠子不知道给谁落了两点墨。
昭然笑嘻嘻地道:“神女开眼,瞧着族长,族长为荡渔村的一族之尊,不就是个大吗?”
赵庸伯脸色微沉地道:“你的意思是我将阿大给藏匿了起来吗?”
“不,不。”昭然道走到祠堂上笑嘻嘻道:“要给祖娘添眼睛,必需踩在供桌上。”
“所以阿大吗?昭然说着缓缓抬起了头,笑道:“就在族长的头顶之上!”
赵庸伯一抬头只见高耸的横梁上横卧着一个人,他一直淡然无波的表情也好似有些抽动。
----
阿大昏厥着被人从横梁上弄了下来,昭然拿起凉水连泼了他几瓢水,他才悠悠地醒来,先是看见了昭然,再看见了赵庸伯连忙道:“族,族长,我,我怎么会在这里的?”
“阿大,我奉你们族长的之命有几句要问你。”昭然蹲身道。
阿大看了一眼赵庸伯,然后有些结巴地道:“你……想问什么?”
“你的证词里说,三年之前,你因为查觉了秀英的私情,所以顾念赵景兄妹无父无母,因此才偷偷地告诉了赵敏儿,对吗?”
阿大挣扎着爬起来连忙道:“正是如此,我可是一片好心。”
“可是事情揭发出来,那阿贵岂不是要难逃罪责,供了偷/情场所给秀英的正是阿贵,你与阿贵经常一起喝酒,情份当比你口中仅是相识的赵敏儿要强太多。”
阿大道:“我,我当时没考虑到这么多,就是不忍心他们兄妹受骗而已。”
“很好,你说告诉我赵敏儿是因为没想太多,那么你把秀英的事情又告诉了阿宽也是因为没想太多吗?”
阿大身体明显一震,昭然道:“在阿宽的供词中交待他每天做完了事,都会出府回到自己的家中,这点想必是事实,也就是说他晚上根本不在赵府,那他是如何得知秀英与赵应文晚上私通这件事情的呢?”
昭然看向阿大:“很简单,你同时告诉了两个人,你知道赵敏儿让赵景确信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,莫过于让他亲眼瞧见,你知道阿宽此人的性格血气方刚,并且做事不择手段,心胸狭隘,有仇必报,他发现秀英暗地里与人私通,必定会因爱生恨,所以他不但强/奸了秀英,并且还择机嫁祸给之前与秀英议婚事的赵景,一箭双雕,以泄心头之恨。你利用了赵敏儿爱护哥哥自己的心,你利用了阿宽的憎恨之心,成功地嫁祸了赵景。”
他转过了头道:“我不是在说阿大,我是在说你——赵相礼。”
赵相礼躺在软椅上,面色相当不好,他握拳连连咳嗽了好几下。
昭然道:“那天是夏至,你留在偏厅里整理礼单,恐怕真正让你留在偏厅里的原因不是这个,你的目的大概是要拖住账房赵应文。当天你大约还会通知阿宽将礼品入库的账本转交给你,以巧妙地告诉他,当晚赵应文会跟你对账目,不可能很快去跟秀英会合,这就给阿宽留下了做案的时间。”
赵庸伯开口道:“赵景不是我府上的人,赵相礼跟他近无仇,远无忧,为什么要构陷于他?”
昭然说道:“这件事我们最后再说,现在来说一说秀英是谁杀的。”
“秀英不是赵应文杀的吗?”
昭然瞧着浑身发抖的赵应文一笑:“这么一个畏首畏尾,只会偷机摸狗的男人,别说给他一个胆子,两个他也未必杀得了秀英。”
他看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人道:“我也曾困惑于秀英是被何人所杀,因为我最初的设想这是个阴谋,阿大将赵景引去,赵景之后被人
他的话音一落,只见牌位后面的布幔被徐徐拉开,露出里面一尊脚踩□□的金塑神女像,所有的村民立即纷纷跪下叩头,现场里站着的便只剩下了杨雪仕跟昭然两个人。
旁边立时有人不悦地道:“请两位也给祖娘行礼。”
昭然脸露为难之色:“老婆子我可是巫王弟子,这要是拜了祖娘,他老人家不高兴了怎办……”
他话还没说完,只见杨雪仕倒是上前作了一揖,上了一柱香,昭然无语,只好跟着也作了一揖,上了一柱香。
赵庸伯一直淡然无语,此时方才道:“今日召各位族老来,为着两桩事,一桩是当年赵景强/奸冤案,一桩是为着秀英身死案。”
族老们齐声道:“听从族长的吩咐。”
“让赵应文,赵敏儿进来。”赵庸伯从盘子中拿出了一块门牌。
昭然将凑过去细看了一下族老们手里的木牌,发现他们手里木牌其实每个人都略有些不同,赵字还有几个细小的数字,显然是为了区别用的。
赵敏儿浑身戴孝地走了进来,身后跟着两个护院拖着赵应文,一个晚上赵应文形貌全毁,头发散乱,双目无神,哪里还有当初斌斌文士的模样,他嘴里不停反复地道:“别杀我,别杀我。”
赵庸伯看着手里的门牌道:“你在府内与绣娘有奸/情可承认?”
“我认,我认。”赵应文浑身哆嗦地道。
“秀英你是怎么杀的?”
赵应文双目无神地道:“她说我如果不休了妻子娶她当正房,她,她就要告发我是□□罪,我一气之下就跟她扭打了起来,然后就将她给掐死了,最后我,我怕她还没死,就用刀子又插了她一刀。”
赵庸伯抬头道:“赵应文通奸罪在前,杀人罪在后,罪大恶极,需报官处理,其家族念其老母稚儿无辜,逐其村落外居住,族老可有异议,若无异议就举牌。”
族老们纷纷举牌,无人有异议。
赵庸伯将手中的木牌丢到了旁边的碳火盆中,赵应文整个人抖成了一团。
杨雪仕见旁边昭然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,他小声问:“你又在想什么?”
昭然却举手道:“我有异议。”
“你又不是荡渔村的人。”旁人道。
昭然嘻嘻地指了一下杨雪仕:“但是你们不是邀请我们大人了吗,那我们总可以提一些意见吧。”
“你又是谁?”
“我是替杨大人说话的人。”昭然理所当然地道。
杨雪仕瞧了他一眼说了两个字道:“不错。”
赵庸伯抬手制止了下面的议论声:“你想说什么?”
昭然笑道:“我想说的话,需要传一个证人。”
“你想传的证人是谁?”
“阿大。”
“阿大……”赵庸伯道,“阿大昨日已经不知去向,你如何传召他?”
“现在我知道他在哪里了,因为有人留了条线索给我。”
“阿大在哪?”族老们议论纷纷。
昭然指着那尊祖娘道:“在那!”
众人抬起头,赵庸伯眼神微微一变,那尊纯金的女神像上眼珠子不知道给谁落了两点墨。
昭然笑嘻嘻地道:“神女开眼,瞧着族长,族长为荡渔村的一族之尊,不就是个大吗?”
赵庸伯脸色微沉地道:“你的意思是我将阿大给藏匿了起来吗?”
“不,不。”昭然道走到祠堂上笑嘻嘻道:“要给祖娘添眼睛,必需踩在供桌上。”
“所以阿大吗?昭然说着缓缓抬起了头,笑道:“就在族长的头顶之上!”
赵庸伯一抬头只见高耸的横梁上横卧着一个人,他一直淡然无波的表情也好似有些抽动。
----
阿大昏厥着被人从横梁上弄了下来,昭然拿起凉水连泼了他几瓢水,他才悠悠地醒来,先是看见了昭然,再看见了赵庸伯连忙道:“族,族长,我,我怎么会在这里的?”
“阿大,我奉你们族长的之命有几句要问你。”昭然蹲身道。
阿大看了一眼赵庸伯,然后有些结巴地道:“你……想问什么?”
“你的证词里说,三年之前,你因为查觉了秀英的私情,所以顾念赵景兄妹无父无母,因此才偷偷地告诉了赵敏儿,对吗?”
阿大挣扎着爬起来连忙道:“正是如此,我可是一片好心。”
“可是事情揭发出来,那阿贵岂不是要难逃罪责,供了偷/情场所给秀英的正是阿贵,你与阿贵经常一起喝酒,情份当比你口中仅是相识的赵敏儿要强太多。”
阿大道:“我,我当时没考虑到这么多,就是不忍心他们兄妹受骗而已。”
“很好,你说告诉我赵敏儿是因为没想太多,那么你把秀英的事情又告诉了阿宽也是因为没想太多吗?”
阿大身体明显一震,昭然道:“在阿宽的供词中交待他每天做完了事,都会出府回到自己的家中,这点想必是事实,也就是说他晚上根本不在赵府,那他是如何得知秀英与赵应文晚上私通这件事情的呢?”
昭然看向阿大:“很简单,你同时告诉了两个人,你知道赵敏儿让赵景确信这件事情的最好办法,莫过于让他亲眼瞧见,你知道阿宽此人的性格血气方刚,并且做事不择手段,心胸狭隘,有仇必报,他发现秀英暗地里与人私通,必定会因爱生恨,所以他不但强/奸了秀英,并且还择机嫁祸给之前与秀英议婚事的赵景,一箭双雕,以泄心头之恨。你利用了赵敏儿爱护哥哥自己的心,你利用了阿宽的憎恨之心,成功地嫁祸了赵景。”
他转过了头道:“我不是在说阿大,我是在说你——赵相礼。”
赵相礼躺在软椅上,面色相当不好,他握拳连连咳嗽了好几下。
昭然道:“那天是夏至,你留在偏厅里整理礼单,恐怕真正让你留在偏厅里的原因不是这个,你的目的大概是要拖住账房赵应文。当天你大约还会通知阿宽将礼品入库的账本转交给你,以巧妙地告诉他,当晚赵应文会跟你对账目,不可能很快去跟秀英会合,这就给阿宽留下了做案的时间。”
赵庸伯开口道:“赵景不是我府上的人,赵相礼跟他近无仇,远无忧,为什么要构陷于他?”
昭然说道:“这件事我们最后再说,现在来说一说秀英是谁杀的。”
“秀英不是赵应文杀的吗?”
昭然瞧着浑身发抖的赵应文一笑:“这么一个畏首畏尾,只会偷机摸狗的男人,别说给他一个胆子,两个他也未必杀得了秀英。”
他看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人道:“我也曾困惑于秀英是被何人所杀,因为我最初的设想这是个阴谋,阿大将赵景引去,赵景之后被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