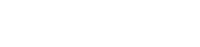个娘们懂什么?若是能……”
他欲言又止,屋内传来女子隐隐的哭泣之声。
----
昭然猫着腰离开,此处靠着港口,来往的船只很多,他沿着江道朝前走,果然不久就找到了间卖吃食的客栈。
即然是阴离的噩梦,那必然跟她落到黑衣男子的手里有关,她此刻多半就在那条贡船之上,他只需要在旁瞧着,黑衣人如何找到贡船,然后再找到阴离即可。
他一踏进客栈的门,迎面便是一阵饭菜香气扑鼻而来,昭然心想,九如所造的梦境还真是逼真,不负噩梦之名。
“客官,您要些什么菜?”小二瞧着昭然衣着华丽连忙上前将他迎到了座位上。
昭然正要开口,却忽然看见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名身着玄衣的书生,腰身细直,他的眼睛不由一亮。
九如!
昭然转身跨前一步,刚要招呼,却见那人的脸半转了过来,乌眉秀目,长相亦是俊雅,却不是九如,而是杨雪仕。
他心中颇有些失望,杨雪仕的眼神浅浅朝着门口扫了一眼,竟是在昭然的脸上一下也未落。
杨雪仕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“我要那张位置。”昭然想了想,指着杨雪仕身后的座位道。
小二将他迎了过去,昭然在杨雪仕的身后坐下,要了酒菜,隔了一会儿,门口走进来一名黄衫的男子,他虽然穿着普通,但身材高大,气势逼人,昭然的眼皮不自然地跳了跳。
王增!
原来靖候府的贡船早就到了,可气那个黑衣汉子居然还一点不知道,一颗珍珠的消息当不会如此,那就是水母在反击了,她让九如噩梦中的船只提前到达了。
“让杨兄久候了。”
“此地简陋,还请王兄不用见怪。”
王增道:“无妨,出门在外,还是随意些的好。”
昭然听着两人寒喧了一番,王增道:“你这番是微服私访,可为何事而来?”
杨雪仕好似顿了顿考道:“我在驻地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,与此处渔村有关,所以返京的路上特来查看一番。”
他显然不愿意细说,王增也便没有细问,转而道:“你此番进京必定高升,只是姜府这般不管不顾地与贵妃对着干,不知道会不会与你有妨碍。”
杨雪仕语气平淡地道:“舍妹虽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,但从小熟读诗书,哪里会愿意去嫁一个乡村匹夫,若非当时我不在家,家父又迫于姜府的权势,这才结下了这门亲事。政见不合,原属平常,但这等亲事却是不能忍,此番回京,雪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退了与那乡野村夫的亲事。”
昭然听他左一句乡村匹夫,右一句乡野村夫,言语平淡,但字里行间极尽鄙视之能,心里陡然就来了气。
他没招着惹着杨雪仕,姜府提亲,他们杨府可应可不应,如今应了却又在背后随意诋毁践踏,这算怎么回事?
“我听说,姜府的外孙是个异人背景。”
杨雪仕冷声道:“怪力乱神,姜子虚就是个装神弄鬼的老匹夫,不足为伍。”
昭然瞧了眼桌面上插在烤肉盘上的刀子,赏了小二一块碎银子,趁着他欣喜的时候就将刀子藏在袖子里走了。
等杨雪仕与王增分手上了楼,昭然撕了一片衣袂将脸蒙住,然后从暗处走了出来,将刀子横在杨雪仕的脖子上,故意恶声恶气地道:“到你房间去,识趣点,老子这会儿正想见血!”
杨雪仕依言打开了自己的屋子,倒也还算镇定地道:“你想要多少钱?”
“那要看你拿多少钱来买命!”昭然故意按着杨雪仕的头,他一抓就把杨雪仕纹丝不乱的头发给弄乱了。
杨雪仕努力挺直了头不卑不亢地道:“这位大侠,我这里的银钱,你看上的尽管取走,但你若伤了我的性命,我乃朝庭命官,只怕此事不会善了。”
昭然瞧着他朝后仰的脖子,细腻的肌肤泛着光泽,再看他束在布带中细直的腰身,心中就恶向胆边,他拿起刀子一挑,割断了杨雪仕的腰带,外头的直缀松散了,里面柔软的细白褒裤就落到了脚踝之处。
他贴着杨雪仕的耳朵道:“我不是大侠,乃一乡野村夫。”
“你,你混账,你敢,你敢……”杨雪仕努力想要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,可惜终究力有不逮。
杨雪仕是当朝有名的美男子,可从出仕以来就官声显赫,身份低的人自然不敢宵想他,身份高的人也不至于为了点美色而得罪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臣子,因此他此生还末遭遇过如此的登徒子。
昭然用手撩开他的下摆故意逗他:“我敢怎么?”
他贴着杨雪仕的身体,用一条腿岔进他的裆中,贴着他耳朵慢条斯理地道:“我怎样了,你又能奈我何?”
杨雪仕只觉得下身一凉,再到两腿中被昭然的一只腿插/入,不禁眼前一黑。
昭然抬眼一瞧,杨雪仕已经是气息不均,手足发软,竟是气得半瘫在了桌子上,再瞧他颇为神似九如的侧面,心中不禁一软,又有些汗颜,连忙粗手笨脚地将裤子替杨雪仕拉上,故意呸了一口:“妈的,老子瞧着长得细肉嫩白的,还以为是个姑娘假扮的呢,竟原来还真是个男人。即不是,也就罢了。”
他走了几步,见杨雪仕依然半伏在桌上,上气不接下气的,有些愧意就又道:“刚才客栈里有三个人在尾随你,他们从南边而来,刚经历过一场战争,三人其中有人最近受过伤,伤在左手,他们所图应该是你身上所携带的文书之类的东西。”
杨雪仕气息好像一下子就平了,他见昭然要从窗口跃出去,居然开口问道:“等等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昭然坐在窗边道:“他们动作利落,应该是行伍出身,此时正是初夏,他们额头却有帽沿,说明是头盔之类的东西留下的,即有头盔,那证明仍然在军。三人都是用右手吃饭,有人却用筷不便,说明他本来应该是用左手,即然放着左手不用,可见那只手应当是受了伤,三个健壮的军人出门,他还伤了手,那多半应该不是打架,而是战争。现在打仗的地方有两处,一处是川上播州,一处是广西瑶人叛乱,所以我说他们是从南边过来。”
杨雪仕咬着牙道:“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所图是我携带的文书之类的东西?”
昭然晃着脚一笑:“三个人进来,那个受伤的军人看了几眼挂在柱子上的条副,可见他认字,一个认字的士兵在军队中怎么也应该是个小吏,再联想到他受了伤还被派出来,可见他们需要一个懂字的人,那当然所图的是你这位朝庭命官身上的需要识字的东西了。政见不同,可不是平常事,有时也会送命的。”
杨雪仕脱口道:“你究竟是谁?”
“噗!”昭然一笑,
他欲言又止,屋内传来女子隐隐的哭泣之声。
----
昭然猫着腰离开,此处靠着港口,来往的船只很多,他沿着江道朝前走,果然不久就找到了间卖吃食的客栈。
即然是阴离的噩梦,那必然跟她落到黑衣男子的手里有关,她此刻多半就在那条贡船之上,他只需要在旁瞧着,黑衣人如何找到贡船,然后再找到阴离即可。
他一踏进客栈的门,迎面便是一阵饭菜香气扑鼻而来,昭然心想,九如所造的梦境还真是逼真,不负噩梦之名。
“客官,您要些什么菜?”小二瞧着昭然衣着华丽连忙上前将他迎到了座位上。
昭然正要开口,却忽然看见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名身着玄衣的书生,腰身细直,他的眼睛不由一亮。
九如!
昭然转身跨前一步,刚要招呼,却见那人的脸半转了过来,乌眉秀目,长相亦是俊雅,却不是九如,而是杨雪仕。
他心中颇有些失望,杨雪仕的眼神浅浅朝着门口扫了一眼,竟是在昭然的脸上一下也未落。
杨雪仕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
“我要那张位置。”昭然想了想,指着杨雪仕身后的座位道。
小二将他迎了过去,昭然在杨雪仕的身后坐下,要了酒菜,隔了一会儿,门口走进来一名黄衫的男子,他虽然穿着普通,但身材高大,气势逼人,昭然的眼皮不自然地跳了跳。
王增!
原来靖候府的贡船早就到了,可气那个黑衣汉子居然还一点不知道,一颗珍珠的消息当不会如此,那就是水母在反击了,她让九如噩梦中的船只提前到达了。
“让杨兄久候了。”
“此地简陋,还请王兄不用见怪。”
王增道:“无妨,出门在外,还是随意些的好。”
昭然听着两人寒喧了一番,王增道:“你这番是微服私访,可为何事而来?”
杨雪仕好似顿了顿考道:“我在驻地发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,与此处渔村有关,所以返京的路上特来查看一番。”
他显然不愿意细说,王增也便没有细问,转而道:“你此番进京必定高升,只是姜府这般不管不顾地与贵妃对着干,不知道会不会与你有妨碍。”
杨雪仕语气平淡地道:“舍妹虽然不是什么大家闺秀,但从小熟读诗书,哪里会愿意去嫁一个乡村匹夫,若非当时我不在家,家父又迫于姜府的权势,这才结下了这门亲事。政见不合,原属平常,但这等亲事却是不能忍,此番回京,雪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退了与那乡野村夫的亲事。”
昭然听他左一句乡村匹夫,右一句乡野村夫,言语平淡,但字里行间极尽鄙视之能,心里陡然就来了气。
他没招着惹着杨雪仕,姜府提亲,他们杨府可应可不应,如今应了却又在背后随意诋毁践踏,这算怎么回事?
“我听说,姜府的外孙是个异人背景。”
杨雪仕冷声道:“怪力乱神,姜子虚就是个装神弄鬼的老匹夫,不足为伍。”
昭然瞧了眼桌面上插在烤肉盘上的刀子,赏了小二一块碎银子,趁着他欣喜的时候就将刀子藏在袖子里走了。
等杨雪仕与王增分手上了楼,昭然撕了一片衣袂将脸蒙住,然后从暗处走了出来,将刀子横在杨雪仕的脖子上,故意恶声恶气地道:“到你房间去,识趣点,老子这会儿正想见血!”
杨雪仕依言打开了自己的屋子,倒也还算镇定地道:“你想要多少钱?”
“那要看你拿多少钱来买命!”昭然故意按着杨雪仕的头,他一抓就把杨雪仕纹丝不乱的头发给弄乱了。
杨雪仕努力挺直了头不卑不亢地道:“这位大侠,我这里的银钱,你看上的尽管取走,但你若伤了我的性命,我乃朝庭命官,只怕此事不会善了。”
昭然瞧着他朝后仰的脖子,细腻的肌肤泛着光泽,再看他束在布带中细直的腰身,心中就恶向胆边,他拿起刀子一挑,割断了杨雪仕的腰带,外头的直缀松散了,里面柔软的细白褒裤就落到了脚踝之处。
他贴着杨雪仕的耳朵道:“我不是大侠,乃一乡野村夫。”
“你,你混账,你敢,你敢……”杨雪仕努力想要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,可惜终究力有不逮。
杨雪仕是当朝有名的美男子,可从出仕以来就官声显赫,身份低的人自然不敢宵想他,身份高的人也不至于为了点美色而得罪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臣子,因此他此生还末遭遇过如此的登徒子。
昭然用手撩开他的下摆故意逗他:“我敢怎么?”
他贴着杨雪仕的身体,用一条腿岔进他的裆中,贴着他耳朵慢条斯理地道:“我怎样了,你又能奈我何?”
杨雪仕只觉得下身一凉,再到两腿中被昭然的一只腿插/入,不禁眼前一黑。
昭然抬眼一瞧,杨雪仕已经是气息不均,手足发软,竟是气得半瘫在了桌子上,再瞧他颇为神似九如的侧面,心中不禁一软,又有些汗颜,连忙粗手笨脚地将裤子替杨雪仕拉上,故意呸了一口:“妈的,老子瞧着长得细肉嫩白的,还以为是个姑娘假扮的呢,竟原来还真是个男人。即不是,也就罢了。”
他走了几步,见杨雪仕依然半伏在桌上,上气不接下气的,有些愧意就又道:“刚才客栈里有三个人在尾随你,他们从南边而来,刚经历过一场战争,三人其中有人最近受过伤,伤在左手,他们所图应该是你身上所携带的文书之类的东西。”
杨雪仕气息好像一下子就平了,他见昭然要从窗口跃出去,居然开口问道:“等等,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昭然坐在窗边道:“他们动作利落,应该是行伍出身,此时正是初夏,他们额头却有帽沿,说明是头盔之类的东西留下的,即有头盔,那证明仍然在军。三人都是用右手吃饭,有人却用筷不便,说明他本来应该是用左手,即然放着左手不用,可见那只手应当是受了伤,三个健壮的军人出门,他还伤了手,那多半应该不是打架,而是战争。现在打仗的地方有两处,一处是川上播州,一处是广西瑶人叛乱,所以我说他们是从南边过来。”
杨雪仕咬着牙道:“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所图是我携带的文书之类的东西?”
昭然晃着脚一笑:“三个人进来,那个受伤的军人看了几眼挂在柱子上的条副,可见他认字,一个认字的士兵在军队中怎么也应该是个小吏,再联想到他受了伤还被派出来,可见他们需要一个懂字的人,那当然所图的是你这位朝庭命官身上的需要识字的东西了。政见不同,可不是平常事,有时也会送命的。”
杨雪仕脱口道:“你究竟是谁?”
“噗!”昭然一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