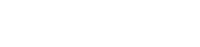宴绥一时被她哭的模样迷了眼。
就像簇赤红的茶花围绕在她的双眸盛开,却又被几滴明澈的泪润饰着,将她眼角的赤色变得浅淡起来。
楚楚可怜的目光下,还有一丝影影绰绰的倔意。
只是这样对付得了关伏,却对付不了像宴绥这种刚开荤,一碰上肉便欲壑难填的人。
余非越是这样的眼神看他,他就越是想狠狠从穴肉里捣烂她,让她目光变得迷醉。
想摧毁凌辱余非的心思漫上他的心头。
宴绥挺动起来的动作更加激烈起来,撞得门都响动起来,余非求他轻点,却被宴绥的一次深入将眼泪顶落。
“你知道吗?”他松开捏着花蒂的手,目光灼灼。
那手慢慢滑落下方,握起她无力垂下的手。
宴绥缓慢地摩挲着她的手掌心,用指尖勾勒出她掌纹的模样:“你越是这样看我,我就越想将你锁起来。”
他再次向上重重顶入,水声伴随余非的娇吟同频响起。
汩汩水液从穴中涌出,沿着那两颗囊袋滑落,液体一滴又一滴的坠地声在静谧的房间内过度清晰。
“怎么办,等一下关伏看见了你要怎么解释?”
宴绥垂眸拍了拍她的臀,让她小穴急促地翕张,酥麻的快感顺着他的后脊蔓延,舒爽得他不禁叹息。
“叫得真好听。”
他夸赞着满面潮红的余非。
欲望就像无底洞一样催使他不断向余非索取,宴绥很享受这一刻余非只能无力地顺从他的感觉。
宴绥扼住她下颚,让她避无可避,只可以承受他唇瓣落下的掠取。
津液交缠的声音太过淫靡。
余非感受到下身的刺激越发激烈,像是要用那根粗长将她死死钉在木门上,她的呼吸被宴绥打乱,唯一可以做的,便只有不断缩紧花穴来缓解快意。
“快点…”余非找准空隙撇开头深呼吸,呜咽着,发出惹人疼惜的声音。
那唇瓣被宴绥吻得像覆了层朦胧春雨。
宴绥目光晦暗,大半的面容匿于阴翳,爱怜地揉着凸起疲惫的花蒂,延长她的快意:“流那么多水,会不会很渴?”
“射外面还是里面好?”
“我要不行了…”余非小腹和腿肚发麻,在他又一次揉过凸起时忍不住颤抖。
宴绥似乎认真沉浸在这个问题上,直到余非无奈捶了他一下,他才终于动起来。
“啵——”
深埋体内的坚挺突然拔出,在她腿间来回蹭着,沾满了淫液的阴茎磨蹭着她鲜妍的地带。
小洞还在发颤翕张,吐出一汪春水。
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,在哭一样。
宴绥按在她花蒂上的手打着小圈,狭长双眸带着促狭:“想我快点结束,就叫大声点。”
但余非哪敢?
她只好用手臂来攀住他,贴在他的耳侧,哼叫起来。
宴绥笑着含住她的耳垂,微凸青筋的手摆弄阴茎的位置,让它在湿透的两瓣不断蹭过。
宴绥不断赞扬她沉溺欲海的证明,直到怀里的人再次抽搐,倒在他怀里,他才伸手撸动射出。
白皙的小腹上流淌着独属他的乳白。
就像浓稠的倒流香,慢慢顺着她曼妙身躯的线条延下。
宴绥不舍地替她擦拭。
可看见它们慢慢落在蜜缝时,旖旎的欲念和他的嫉妒又作祟起来。
宴绥拿着纸巾替她擦拭的动作停顿了很久。
直到他看见木制床头柜上的手机,亮着屏幕响动了三秒,又匆匆挂断。
“萧隽…”惊人的发现,让宴绥沉声笑了起来,他摩挲着余非的唇瓣,忽然有了其他主意。
就像簇赤红的茶花围绕在她的双眸盛开,却又被几滴明澈的泪润饰着,将她眼角的赤色变得浅淡起来。
楚楚可怜的目光下,还有一丝影影绰绰的倔意。
只是这样对付得了关伏,却对付不了像宴绥这种刚开荤,一碰上肉便欲壑难填的人。
余非越是这样的眼神看他,他就越是想狠狠从穴肉里捣烂她,让她目光变得迷醉。
想摧毁凌辱余非的心思漫上他的心头。
宴绥挺动起来的动作更加激烈起来,撞得门都响动起来,余非求他轻点,却被宴绥的一次深入将眼泪顶落。
“你知道吗?”他松开捏着花蒂的手,目光灼灼。
那手慢慢滑落下方,握起她无力垂下的手。
宴绥缓慢地摩挲着她的手掌心,用指尖勾勒出她掌纹的模样:“你越是这样看我,我就越想将你锁起来。”
他再次向上重重顶入,水声伴随余非的娇吟同频响起。
汩汩水液从穴中涌出,沿着那两颗囊袋滑落,液体一滴又一滴的坠地声在静谧的房间内过度清晰。
“怎么办,等一下关伏看见了你要怎么解释?”
宴绥垂眸拍了拍她的臀,让她小穴急促地翕张,酥麻的快感顺着他的后脊蔓延,舒爽得他不禁叹息。
“叫得真好听。”
他夸赞着满面潮红的余非。
欲望就像无底洞一样催使他不断向余非索取,宴绥很享受这一刻余非只能无力地顺从他的感觉。
宴绥扼住她下颚,让她避无可避,只可以承受他唇瓣落下的掠取。
津液交缠的声音太过淫靡。
余非感受到下身的刺激越发激烈,像是要用那根粗长将她死死钉在木门上,她的呼吸被宴绥打乱,唯一可以做的,便只有不断缩紧花穴来缓解快意。
“快点…”余非找准空隙撇开头深呼吸,呜咽着,发出惹人疼惜的声音。
那唇瓣被宴绥吻得像覆了层朦胧春雨。
宴绥目光晦暗,大半的面容匿于阴翳,爱怜地揉着凸起疲惫的花蒂,延长她的快意:“流那么多水,会不会很渴?”
“射外面还是里面好?”
“我要不行了…”余非小腹和腿肚发麻,在他又一次揉过凸起时忍不住颤抖。
宴绥似乎认真沉浸在这个问题上,直到余非无奈捶了他一下,他才终于动起来。
“啵——”
深埋体内的坚挺突然拔出,在她腿间来回蹭着,沾满了淫液的阴茎磨蹭着她鲜妍的地带。
小洞还在发颤翕张,吐出一汪春水。
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,在哭一样。
宴绥按在她花蒂上的手打着小圈,狭长双眸带着促狭:“想我快点结束,就叫大声点。”
但余非哪敢?
她只好用手臂来攀住他,贴在他的耳侧,哼叫起来。
宴绥笑着含住她的耳垂,微凸青筋的手摆弄阴茎的位置,让它在湿透的两瓣不断蹭过。
宴绥不断赞扬她沉溺欲海的证明,直到怀里的人再次抽搐,倒在他怀里,他才伸手撸动射出。
白皙的小腹上流淌着独属他的乳白。
就像浓稠的倒流香,慢慢顺着她曼妙身躯的线条延下。
宴绥不舍地替她擦拭。
可看见它们慢慢落在蜜缝时,旖旎的欲念和他的嫉妒又作祟起来。
宴绥拿着纸巾替她擦拭的动作停顿了很久。
直到他看见木制床头柜上的手机,亮着屏幕响动了三秒,又匆匆挂断。
“萧隽…”惊人的发现,让宴绥沉声笑了起来,他摩挲着余非的唇瓣,忽然有了其他主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