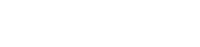楚领五郡,独立世间,楚人眼中的世界便与世间人有大分别:日当空是炎帝当空,风过耳是飞廉过耳;雨雹失常,则不大好,是雨师失常,需要平息神怒,于是人们裸胸奔走,在宫台前大呼:“萍翳!”
萍翳是雨师名,楚人懂,文鸢不懂。她在连阁徘徊,忐忑地等待。
约一刻以后,雨渐小,连阁尽头的门突然被推开。
一名宫人喊:“欸!”
文鸢吓着,急忙转身,宫人却比她还害怕,竟逃走了。两人在连阁上逶迤,最后还是文鸢喊住他:“何事呢?”
“楚王恰好去了云梦,一时回不来,你,先随我去吃饭。”宫人赤红耳朵。
晚餐鹿、兔与红枣。文鸢吃饭时,幕人掀开帘幕,露出叁四张宫人脸。
文鸢不自在,去看他们。他们便推搡,往帘子后面躲,都是赤红耳朵。
又一刻,水仙送到文鸢脚边。
饮食,沐浴,休息……文鸢在楚宫殿里过夜,听郢都的风声。
她睡不着,总担心楚王何时归来,便循宫灯夜游。灯火照亮壁画,一墙龙凤山鬼,乱了文鸢的眼睛。
她目眩,绕着旋室走了很久,才发现室内有巨幅的画像,将空间辟成两半,她在这一半,值夜人在另一半,已经熟睡。
“对于他们来说,值夜就是倚着凳子睡觉吗?”文鸢这样想,捂了嘴巴绕到画的正面:一幅二人对弈的图画,女子愤怒状,形貌夸张,牙齿画成獠牙,双手画成利爪,然而首服却很华丽;男子惶恐状,跪地张口,似乎在解释,又像在讨饶。
怪画。
看久了,异样的感觉袭人。文鸢想回去,一转身,踢翻小几,以为酿成大祸,急忙蹲下。
楚宫人睡得沉,恍若身处福地,绝不会有危险降临。
同一时刻,毗邻楚王国的东海郡中,太守桓繁露却做出不同的判断:“楚国危。”
他抓来瞭望的人,仔细询问;又查验郤梅的通行凭证:“十二力士,出身渭水两岸、河东、河西、雁门……”
属下不敢说话,在一侧看长官收紧的后腮。天边泛白,他们困得不行,强打精神,忽然被桓繁露踢开,吓得喊:“大人!”
桓繁露负手站在门前,气势与杀人时同。
省中赐下的礼物早已到达,想必那女子今后不是与楚王并肩,就是在楚王的床榻,他这次也恪守本职,消灭了一切关联人物,却莫名觉得失职,似乎漏掉了什么关节处,不过无论怎么查,也查不出漏,只好看看风景:朝霞染了楚王城,令人生厌。
“遣使去云梦,”桓繁露说,又挥手驳斥自己,“不行,我去。”
大水、大泽、山溪相汇,白气冲上天空,再落下时,由楚人称为“梦”的湖泊接住。这里是上古名苑,数薮围出千里滩泽,水源广布,壮阔以云梦为最。且与洞庭交接,通达数郡,不设高墙,也是桓繁露唯一能够对话楚王的地方。
他交印与长沙郡驻军,步行至水陆之间。
长途跋涉不能阻挠他,轻飘飘的雾却让他呼吸困难。且因雾中有一个身影,隔湖间树,类云中君,却有人的修匀——桓繁露几乎屏息,伏在地上:“楚王殿下。”
“繁露。”湖水传声。
“不出正月,云梦依然有深瘴,殿下不好久住。”出行时的焦躁没了,桓繁露像一位慈母。
“多谢繁露,”有笑声,“虽这样说,我已经在云梦住了十余天,瘴湿只好回去再治。”
桓繁露不苟言笑,却是江汉人,血脉中天然有对楚王的爱。听到他故意呛自己,桓繁露依旧温和:“殿下总是这样……”
“繁露来云梦何事呢。”
“对了,殿下,”一阵狂风,一阵土腥,将桓繁露吹醒,“回到王居以后,要处处留心。我懈怠,或许将危险放入楚国境了。”
“又是危险,”不知世事险恶的人,与桓繁露玩笑,“上次你来云梦,说有危险,我回国都,查到黄鹂入境,和它们一同赴歌舞。”
“然而这回也可能是鹰!”
“鹰?鹰好啊。请让你们久居国中的寡君见一见鹰,”一只手拨开白雾,纹绮乍现,“不然,如何能被你们唤作‘云中君’?”
桓繁露还想再劝,楚王已经从林中走出,隔着半面湖水微笑:他来云梦养性,通身隐花孔雀,脚边一对凫,湖风起,便成仙人飘堕。
桓繁露说不出什么了,流着汗,再拜他一次:“楚王……”
“殿下!”声音从湖另一侧来。
是楚内地的使者,来告知楚王省中有礼。
“是吗,那么我久留云梦,已经失礼了。父皇可有来信?没有,唔,父皇理政,何时有空,给我写个字条都好。”楚王拾起衣袖,与水鸟作别。
横跨一湖,桓繁露听不清使者的话,但见楚王愉快着、忙碌着,已经猜到原委:“殿下,即便女子是省中赠礼,也不能与她过于亲热,失去尊卑。”
湖心无声,人似乎走了。
桓繁露叹口气,也要走,忽然看到水面荡过一朵水仙花。
“繁露,我能安居国中,多亏有你,花送你做谢礼。你的话我句句都听,到郢都了就会实行。所以与我分别当夜,你可以免操劳我,更照料自己。”王随使者离去,剩下一名高八尺的壮汉,手捧水仙,模样滑稽。
长沙郡的驻兵被逗笑,想与桓繁露攀谈,目及其面色,吓一大跳,似乎楚王走,所有亲热都走,这才想起东海守原来是什么样的人,立刻司职守卫。
轻车过平原,带回一位国王。他从容,横穿郢都时像风。
王居脚下的民众说:“我君太慢,少女等了近半月。”楚王抱歉,拆分玉组佩送给众人,后来又抽掉发间的绦带。
他散发入宫,进殿时,第一眼就看见文鸢。
文鸢抱着白兔,正听楚宫人传授辨雌雄的方法:“扑朔迷离并不难人,将手放在兔腹,大概度量……”
她穿楚服,戴楚饰,已经与宫人相熟,却头一次遇见国君。
两人都发愣。
铜漏下水五刻,宫人先行备餐。楚王从他们中间过,轻声应着“辛苦”“久等”,来到文鸢面前。殿内闪烁,夔龙与云刻沦为背景,文鸢见识到以庞丽的宫殿做陪衬的王:她的亲哥哥。
“王兄。”
文鸢声音小,又埋着头,楚王不得不躬身。
“王——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他友善地笑。
“王殿下,楚王殿下,”文鸢张口结舌,下一刻清醒,连忙说出息再准备的化名,“我叫知岁。”
“好名字,”楚王接过兔子,帮她拍拂袖口,“午饭吧,知岁,不早了。”
文鸢彻冷,仿佛回到还在飘雪的季冬月。
季冬月,息再告诉她:“不能让楚王知道你的身份。”
他们从灵飞出发,彼时距省中不到十里。车马走在雪上,留下两行深辙,给松鼠栖身。
“为什么?”文鸢少有回嘴的时刻。
看到息再挑眉,她才嗫嚅着解释:“楚王不知我的样貌,可他毕竟是我长兄,世上无二的男子。不告诉他,便没有可以告诉的人了。”
息再的表情耐人寻味。文鸢以为他生气。
但她退到车厢内,借雪耀眼的光,又能看清他的脸:有些落寞。
“我们有过承诺,你的命归我,”他用落寞的表情斥人,靠近一些,“按我说的做,不使自己的性命流失,就是你的守信。”
两人有过一次肌肤亲,一次唇齿的交融,彼此的呼吸重了,都能感应。当下文鸢垂眼,避开他的视线,却更紧张,目光恰好平视男子喉间。
骨感的喉结,滑动得轻。
文鸢想起某个绮靡的时刻,这段喉结曾在眼前重重滚落。
她慌忙去看别处。
息再不强迫她,改骑马,走前:“带你见一个人。”
人在队伍中后,乘坐息再的车驾。文鸢由息再扶进去,让厢内明明暗暗,打搅人醒。他皱起眉,看清文鸢,又舒眉。
有雪进窗。他去关窗,被文鸢抓住手指。
“怎么?”
抓住手指的人摇头,改抱臂膀。
文鸢知道他一直在。
从左冯翊出发时,文鸢看到出众而超群的身量。她忘乎所以,想去找他,被息再按到车里,等到今天。
“恩人。”文鸢稚子一样高兴。
晏待时便觉得一种长久缺失的、人的情感回到心中,也动了嘴角。
然而下一刻,文鸢将他的手放在咽喉处,又让晏待时沉心。
他顺势掐住文鸢的脖颈,将她朝厢壁按。文鸢不反抗,只是流泪。
动静传到厢外。息再骑马,与车并行。
“当时让我死绝,现在就不会有麻烦。”晏待时用了点力。
文鸢屏息,抓住他的手,一方面引颈受戮,一方面又想脱身:“如我递箭时所说,我真的做出恩将仇报的事,请恩人了断。”
“那么这就算是你的了断。”在人晕倒前,晏待时及时松开,抚摸她颈上的指印,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腰:两人从一个困境挣扎,一场血斗里逃出,一样清癯又孑然。
文鸢埋进他怀里,大口喘气:“恩人出了宫,了断我,之后天南地北,千万不要回沙丘。”
晏待时愣住,之后苦笑。
他第一次相信外人能够彻底解放自己:“当然,我的命已经属于你。”
帘幕掀动,车内外叁人的目光缠在一起。
晏待时拍拍文鸢的脊背:“不要告诉楚王,你是文鸢公主。”
文鸢不解,过后询问,得到晏待时的解答:“为保护他,也为保护你。”
保护他,保护我……
文鸢随楚王去用餐,看着他的背影发愣。
楚国是仙话里的王国,严军要塞围出的世外地,人生活在其中,纯真如自然物,侍奉唯一一位神王。还需要保护什么呢,如今最危险的,大概就是悄声入楚的晏待时自己了。
文鸢想着,发现楚王侧目在看自己,连忙跟上。
萍翳是雨师名,楚人懂,文鸢不懂。她在连阁徘徊,忐忑地等待。
约一刻以后,雨渐小,连阁尽头的门突然被推开。
一名宫人喊:“欸!”
文鸢吓着,急忙转身,宫人却比她还害怕,竟逃走了。两人在连阁上逶迤,最后还是文鸢喊住他:“何事呢?”
“楚王恰好去了云梦,一时回不来,你,先随我去吃饭。”宫人赤红耳朵。
晚餐鹿、兔与红枣。文鸢吃饭时,幕人掀开帘幕,露出叁四张宫人脸。
文鸢不自在,去看他们。他们便推搡,往帘子后面躲,都是赤红耳朵。
又一刻,水仙送到文鸢脚边。
饮食,沐浴,休息……文鸢在楚宫殿里过夜,听郢都的风声。
她睡不着,总担心楚王何时归来,便循宫灯夜游。灯火照亮壁画,一墙龙凤山鬼,乱了文鸢的眼睛。
她目眩,绕着旋室走了很久,才发现室内有巨幅的画像,将空间辟成两半,她在这一半,值夜人在另一半,已经熟睡。
“对于他们来说,值夜就是倚着凳子睡觉吗?”文鸢这样想,捂了嘴巴绕到画的正面:一幅二人对弈的图画,女子愤怒状,形貌夸张,牙齿画成獠牙,双手画成利爪,然而首服却很华丽;男子惶恐状,跪地张口,似乎在解释,又像在讨饶。
怪画。
看久了,异样的感觉袭人。文鸢想回去,一转身,踢翻小几,以为酿成大祸,急忙蹲下。
楚宫人睡得沉,恍若身处福地,绝不会有危险降临。
同一时刻,毗邻楚王国的东海郡中,太守桓繁露却做出不同的判断:“楚国危。”
他抓来瞭望的人,仔细询问;又查验郤梅的通行凭证:“十二力士,出身渭水两岸、河东、河西、雁门……”
属下不敢说话,在一侧看长官收紧的后腮。天边泛白,他们困得不行,强打精神,忽然被桓繁露踢开,吓得喊:“大人!”
桓繁露负手站在门前,气势与杀人时同。
省中赐下的礼物早已到达,想必那女子今后不是与楚王并肩,就是在楚王的床榻,他这次也恪守本职,消灭了一切关联人物,却莫名觉得失职,似乎漏掉了什么关节处,不过无论怎么查,也查不出漏,只好看看风景:朝霞染了楚王城,令人生厌。
“遣使去云梦,”桓繁露说,又挥手驳斥自己,“不行,我去。”
大水、大泽、山溪相汇,白气冲上天空,再落下时,由楚人称为“梦”的湖泊接住。这里是上古名苑,数薮围出千里滩泽,水源广布,壮阔以云梦为最。且与洞庭交接,通达数郡,不设高墙,也是桓繁露唯一能够对话楚王的地方。
他交印与长沙郡驻军,步行至水陆之间。
长途跋涉不能阻挠他,轻飘飘的雾却让他呼吸困难。且因雾中有一个身影,隔湖间树,类云中君,却有人的修匀——桓繁露几乎屏息,伏在地上:“楚王殿下。”
“繁露。”湖水传声。
“不出正月,云梦依然有深瘴,殿下不好久住。”出行时的焦躁没了,桓繁露像一位慈母。
“多谢繁露,”有笑声,“虽这样说,我已经在云梦住了十余天,瘴湿只好回去再治。”
桓繁露不苟言笑,却是江汉人,血脉中天然有对楚王的爱。听到他故意呛自己,桓繁露依旧温和:“殿下总是这样……”
“繁露来云梦何事呢。”
“对了,殿下,”一阵狂风,一阵土腥,将桓繁露吹醒,“回到王居以后,要处处留心。我懈怠,或许将危险放入楚国境了。”
“又是危险,”不知世事险恶的人,与桓繁露玩笑,“上次你来云梦,说有危险,我回国都,查到黄鹂入境,和它们一同赴歌舞。”
“然而这回也可能是鹰!”
“鹰?鹰好啊。请让你们久居国中的寡君见一见鹰,”一只手拨开白雾,纹绮乍现,“不然,如何能被你们唤作‘云中君’?”
桓繁露还想再劝,楚王已经从林中走出,隔着半面湖水微笑:他来云梦养性,通身隐花孔雀,脚边一对凫,湖风起,便成仙人飘堕。
桓繁露说不出什么了,流着汗,再拜他一次:“楚王……”
“殿下!”声音从湖另一侧来。
是楚内地的使者,来告知楚王省中有礼。
“是吗,那么我久留云梦,已经失礼了。父皇可有来信?没有,唔,父皇理政,何时有空,给我写个字条都好。”楚王拾起衣袖,与水鸟作别。
横跨一湖,桓繁露听不清使者的话,但见楚王愉快着、忙碌着,已经猜到原委:“殿下,即便女子是省中赠礼,也不能与她过于亲热,失去尊卑。”
湖心无声,人似乎走了。
桓繁露叹口气,也要走,忽然看到水面荡过一朵水仙花。
“繁露,我能安居国中,多亏有你,花送你做谢礼。你的话我句句都听,到郢都了就会实行。所以与我分别当夜,你可以免操劳我,更照料自己。”王随使者离去,剩下一名高八尺的壮汉,手捧水仙,模样滑稽。
长沙郡的驻兵被逗笑,想与桓繁露攀谈,目及其面色,吓一大跳,似乎楚王走,所有亲热都走,这才想起东海守原来是什么样的人,立刻司职守卫。
轻车过平原,带回一位国王。他从容,横穿郢都时像风。
王居脚下的民众说:“我君太慢,少女等了近半月。”楚王抱歉,拆分玉组佩送给众人,后来又抽掉发间的绦带。
他散发入宫,进殿时,第一眼就看见文鸢。
文鸢抱着白兔,正听楚宫人传授辨雌雄的方法:“扑朔迷离并不难人,将手放在兔腹,大概度量……”
她穿楚服,戴楚饰,已经与宫人相熟,却头一次遇见国君。
两人都发愣。
铜漏下水五刻,宫人先行备餐。楚王从他们中间过,轻声应着“辛苦”“久等”,来到文鸢面前。殿内闪烁,夔龙与云刻沦为背景,文鸢见识到以庞丽的宫殿做陪衬的王:她的亲哥哥。
“王兄。”
文鸢声音小,又埋着头,楚王不得不躬身。
“王——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他友善地笑。
“王殿下,楚王殿下,”文鸢张口结舌,下一刻清醒,连忙说出息再准备的化名,“我叫知岁。”
“好名字,”楚王接过兔子,帮她拍拂袖口,“午饭吧,知岁,不早了。”
文鸢彻冷,仿佛回到还在飘雪的季冬月。
季冬月,息再告诉她:“不能让楚王知道你的身份。”
他们从灵飞出发,彼时距省中不到十里。车马走在雪上,留下两行深辙,给松鼠栖身。
“为什么?”文鸢少有回嘴的时刻。
看到息再挑眉,她才嗫嚅着解释:“楚王不知我的样貌,可他毕竟是我长兄,世上无二的男子。不告诉他,便没有可以告诉的人了。”
息再的表情耐人寻味。文鸢以为他生气。
但她退到车厢内,借雪耀眼的光,又能看清他的脸:有些落寞。
“我们有过承诺,你的命归我,”他用落寞的表情斥人,靠近一些,“按我说的做,不使自己的性命流失,就是你的守信。”
两人有过一次肌肤亲,一次唇齿的交融,彼此的呼吸重了,都能感应。当下文鸢垂眼,避开他的视线,却更紧张,目光恰好平视男子喉间。
骨感的喉结,滑动得轻。
文鸢想起某个绮靡的时刻,这段喉结曾在眼前重重滚落。
她慌忙去看别处。
息再不强迫她,改骑马,走前:“带你见一个人。”
人在队伍中后,乘坐息再的车驾。文鸢由息再扶进去,让厢内明明暗暗,打搅人醒。他皱起眉,看清文鸢,又舒眉。
有雪进窗。他去关窗,被文鸢抓住手指。
“怎么?”
抓住手指的人摇头,改抱臂膀。
文鸢知道他一直在。
从左冯翊出发时,文鸢看到出众而超群的身量。她忘乎所以,想去找他,被息再按到车里,等到今天。
“恩人。”文鸢稚子一样高兴。
晏待时便觉得一种长久缺失的、人的情感回到心中,也动了嘴角。
然而下一刻,文鸢将他的手放在咽喉处,又让晏待时沉心。
他顺势掐住文鸢的脖颈,将她朝厢壁按。文鸢不反抗,只是流泪。
动静传到厢外。息再骑马,与车并行。
“当时让我死绝,现在就不会有麻烦。”晏待时用了点力。
文鸢屏息,抓住他的手,一方面引颈受戮,一方面又想脱身:“如我递箭时所说,我真的做出恩将仇报的事,请恩人了断。”
“那么这就算是你的了断。”在人晕倒前,晏待时及时松开,抚摸她颈上的指印,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腰:两人从一个困境挣扎,一场血斗里逃出,一样清癯又孑然。
文鸢埋进他怀里,大口喘气:“恩人出了宫,了断我,之后天南地北,千万不要回沙丘。”
晏待时愣住,之后苦笑。
他第一次相信外人能够彻底解放自己:“当然,我的命已经属于你。”
帘幕掀动,车内外叁人的目光缠在一起。
晏待时拍拍文鸢的脊背:“不要告诉楚王,你是文鸢公主。”
文鸢不解,过后询问,得到晏待时的解答:“为保护他,也为保护你。”
保护他,保护我……
文鸢随楚王去用餐,看着他的背影发愣。
楚国是仙话里的王国,严军要塞围出的世外地,人生活在其中,纯真如自然物,侍奉唯一一位神王。还需要保护什么呢,如今最危险的,大概就是悄声入楚的晏待时自己了。
文鸢想着,发现楚王侧目在看自己,连忙跟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