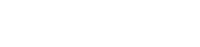陌生人
在下山时,云初总有一种被视线注视着的不适应感,但是回头看又发现不了来源——每次一回过头,那种强烈的视线似乎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于是她只能有些迟疑地继续往住所走着,刚抬脚,她猛地一回头,却依旧没看到什么人的身影。
嘶……闹鬼了?
云初本来是不怕这种东西的,但是只限于原本的世界……这个世界可是真的会有鬼的,她不敢放松警惕,只能加快了脚步,远远的看见了自己家的院门,似乎是有了希望,步伐也跟着有力起来。
咔嚓。
好像是……落叶被踩碎的声音?
云初回头,这次虽然没看到人,但不远处的碎掉的落叶似乎昭显着,好像是有人在跟着他……而不是更危险的鬼魂。
云初开始感到一阵安心,只要是人就好应付多了,至于是谁她也不在乎。只要不影响她,这个人一直跟着她也没什么影响——宗门里是很安全的。而且就算有事相告,也会直接出现在她面前的,既然一直不出现,也许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
云初想明白了逻辑,也没了心理负担放缓了速度,身后那个不知道身份却一直跟着她的人也放缓了速度,而且他似乎意识到了她的发觉,也不尝试掩饰了,身后踩树叶的声音也明显的变多起来,穿过了最后一片树林,再走大概五分钟,就可以到家了。
云初停了下来,但这次她没有尝试回头,只是站在原地开口。
“我快要到家了……如果你找我有事,现在是你最后一次出现的机会了。”
树林里一片寂静。
“好吧……”也没有很出乎意料的反应,她抬步,走上了最后一段回家的路。
“再见啦,陌生人。”
她的头上身上还沾着没掸下去的落叶,脆的枯萎的又是金黄的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她走的坚定又孤单,而又显出了几分圣洁来。
可是她并不是神祇。
在树干的阴影中,他握紧了爪子,指甲狠狠地嵌入血肉,他却毫无知觉的攥的紧一些,再紧一些,仿佛只有疼痛才会给他带来最原始的感觉。血液顺着手指滴落到地上,粘上树叶的金黄,他垂下眼睑,若有所思的看着地上被染成暗红色的树叶,如果把这血液抹到云初脸上,她会露出什么表情?依旧是虚伪的帮他包扎,还是被血腥气息熏得作呕,厌恶的模样毫不掩饰?
澈溪想,他大概是让云初逼疯了。那日他睁开眼睛,偏过头看到的不是那个弃他如敝的人,女孩泪汪汪的伸出手,身上的气味熏的他又想打一个喷嚏。
“云轻……姐姐,”他说,“你能放开我的手吗?”
“啊……”女孩擦掉泪水,故作关心的把手放到了他的头上,“澈溪,你感觉身体怎么样了?”
她的声音是有几分像云初的,澈溪想,放柔了声音就更像了,云初说话总是没有气势的,和他生气争辩也像是在撒娇认错,但每次听完了话语的内容又觉得心寒。但云初的声音就是云初的,是没有替代品的感受,他拨下去那只放到他额头上的手,但表面功夫做的还是很足,软声细语的对云轻说话。
“我没事的,”他低下了头,一副雨打湿的可怜模样,“谢谢云轻姐姐的关心……”
表面可怜巴巴,内心毫无波澜,澈溪骨子里就是这种人,要在野外生存下来谁管你仁义礼治,他的灵智开的过早,后期的理学感化便总是局限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,有了那份心思就装一装,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很显然的没了那份心思,又变回了野外孤独的那匹小狼,在野兽面前俯首称臣,在卸下防御后再腾空而起,咬断野兽的咽喉。
或许比起自己流血,澈溪更想看云初流血,他要咬住云初的喉管,看着她的血液喷涌而出全都洒到他的身上。小狼狠狠地颤抖了一下,似乎是真的感受到了那温热的血液洒在身上,他的心脏早已麻木,只有手心传来丝丝凉意,才勉强抬手看了一眼,似乎有些过了头,他终于放弃了折磨手上那块皮肤,本来就没有愈合完全的伤口又被扣开,直到再也看不出另一个人的包扎痕迹。
真是让人不快,澈溪又不满意起来,尾巴焦躁的在身后摆弄扫地,云初明明在他的过去留下了那么浓墨重彩的一笔,她居然忘记的这么彻底,直接奔向了一段新的生活,一个新捡回来的替代品。
但是澈溪又想起了刚刚云初那个样子,她最后告别时尾音上扬,大概是不知道他的身份才说的轻松柔和,但也说不来的安抚了他的情绪。他不满地从嗓子里发出几声呜咽嘶吼,兽需要的不只有这点牙缝都塞不满的小利,但在不表明身份的前提下,他能得到的也只有这些。
他抬脚,最后踩碎了一片落叶,碎片没入血泊,他神色不明的最后看一眼,才转身往回走。
—
“阿青——”
云初推开门,出门时她和阿青打过招呼了,扫一眼,就能看到树下的石桌旁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,闻言,他放下了手里摆弄的东西,回过头稳稳当当的接住了屈膝扑到怀里的她。
“怎么了?”
云初有些疲惫的在他怀里蹭了又蹭,直到那熟悉的草香又一次包裹她的身躯。果然,还是这里最让她放松,不用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,放下一切的去全心全意的依靠另一个人的身躯。
“没事……”她埋在男人的胸膛里,声音闷闷的,“我只是在想,我的阿青是世上最完美的夫君。”
……好明显的心跳声,大概耳朵也很红了吧,云初笑了出来,但她决定,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抬头了——给自己的夫君留下最后一丝薄面。
—
疯狗,羞树,累人(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做标题啊可恶)
恭喜臭狗从妄想症进入下一个阶段(澈溪:爷是狼!)
--
嘶……闹鬼了?
云初本来是不怕这种东西的,但是只限于原本的世界……这个世界可是真的会有鬼的,她不敢放松警惕,只能加快了脚步,远远的看见了自己家的院门,似乎是有了希望,步伐也跟着有力起来。
咔嚓。
好像是……落叶被踩碎的声音?
云初回头,这次虽然没看到人,但不远处的碎掉的落叶似乎昭显着,好像是有人在跟着他……而不是更危险的鬼魂。
云初开始感到一阵安心,只要是人就好应付多了,至于是谁她也不在乎。只要不影响她,这个人一直跟着她也没什么影响——宗门里是很安全的。而且就算有事相告,也会直接出现在她面前的,既然一直不出现,也许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
云初想明白了逻辑,也没了心理负担放缓了速度,身后那个不知道身份却一直跟着她的人也放缓了速度,而且他似乎意识到了她的发觉,也不尝试掩饰了,身后踩树叶的声音也明显的变多起来,穿过了最后一片树林,再走大概五分钟,就可以到家了。
云初停了下来,但这次她没有尝试回头,只是站在原地开口。
“我快要到家了……如果你找我有事,现在是你最后一次出现的机会了。”
树林里一片寂静。
“好吧……”也没有很出乎意料的反应,她抬步,走上了最后一段回家的路。
“再见啦,陌生人。”
她的头上身上还沾着没掸下去的落叶,脆的枯萎的又是金黄的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她走的坚定又孤单,而又显出了几分圣洁来。
可是她并不是神祇。
在树干的阴影中,他握紧了爪子,指甲狠狠地嵌入血肉,他却毫无知觉的攥的紧一些,再紧一些,仿佛只有疼痛才会给他带来最原始的感觉。血液顺着手指滴落到地上,粘上树叶的金黄,他垂下眼睑,若有所思的看着地上被染成暗红色的树叶,如果把这血液抹到云初脸上,她会露出什么表情?依旧是虚伪的帮他包扎,还是被血腥气息熏得作呕,厌恶的模样毫不掩饰?
澈溪想,他大概是让云初逼疯了。那日他睁开眼睛,偏过头看到的不是那个弃他如敝的人,女孩泪汪汪的伸出手,身上的气味熏的他又想打一个喷嚏。
“云轻……姐姐,”他说,“你能放开我的手吗?”
“啊……”女孩擦掉泪水,故作关心的把手放到了他的头上,“澈溪,你感觉身体怎么样了?”
她的声音是有几分像云初的,澈溪想,放柔了声音就更像了,云初说话总是没有气势的,和他生气争辩也像是在撒娇认错,但每次听完了话语的内容又觉得心寒。但云初的声音就是云初的,是没有替代品的感受,他拨下去那只放到他额头上的手,但表面功夫做的还是很足,软声细语的对云轻说话。
“我没事的,”他低下了头,一副雨打湿的可怜模样,“谢谢云轻姐姐的关心……”
表面可怜巴巴,内心毫无波澜,澈溪骨子里就是这种人,要在野外生存下来谁管你仁义礼治,他的灵智开的过早,后期的理学感化便总是局限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,有了那份心思就装一装,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很显然的没了那份心思,又变回了野外孤独的那匹小狼,在野兽面前俯首称臣,在卸下防御后再腾空而起,咬断野兽的咽喉。
或许比起自己流血,澈溪更想看云初流血,他要咬住云初的喉管,看着她的血液喷涌而出全都洒到他的身上。小狼狠狠地颤抖了一下,似乎是真的感受到了那温热的血液洒在身上,他的心脏早已麻木,只有手心传来丝丝凉意,才勉强抬手看了一眼,似乎有些过了头,他终于放弃了折磨手上那块皮肤,本来就没有愈合完全的伤口又被扣开,直到再也看不出另一个人的包扎痕迹。
真是让人不快,澈溪又不满意起来,尾巴焦躁的在身后摆弄扫地,云初明明在他的过去留下了那么浓墨重彩的一笔,她居然忘记的这么彻底,直接奔向了一段新的生活,一个新捡回来的替代品。
但是澈溪又想起了刚刚云初那个样子,她最后告别时尾音上扬,大概是不知道他的身份才说的轻松柔和,但也说不来的安抚了他的情绪。他不满地从嗓子里发出几声呜咽嘶吼,兽需要的不只有这点牙缝都塞不满的小利,但在不表明身份的前提下,他能得到的也只有这些。
他抬脚,最后踩碎了一片落叶,碎片没入血泊,他神色不明的最后看一眼,才转身往回走。
—
“阿青——”
云初推开门,出门时她和阿青打过招呼了,扫一眼,就能看到树下的石桌旁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,闻言,他放下了手里摆弄的东西,回过头稳稳当当的接住了屈膝扑到怀里的她。
“怎么了?”
云初有些疲惫的在他怀里蹭了又蹭,直到那熟悉的草香又一次包裹她的身躯。果然,还是这里最让她放松,不用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,放下一切的去全心全意的依靠另一个人的身躯。
“没事……”她埋在男人的胸膛里,声音闷闷的,“我只是在想,我的阿青是世上最完美的夫君。”
……好明显的心跳声,大概耳朵也很红了吧,云初笑了出来,但她决定,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抬头了——给自己的夫君留下最后一丝薄面。
—
疯狗,羞树,累人(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做标题啊可恶)
恭喜臭狗从妄想症进入下一个阶段(澈溪:爷是狼!)
--